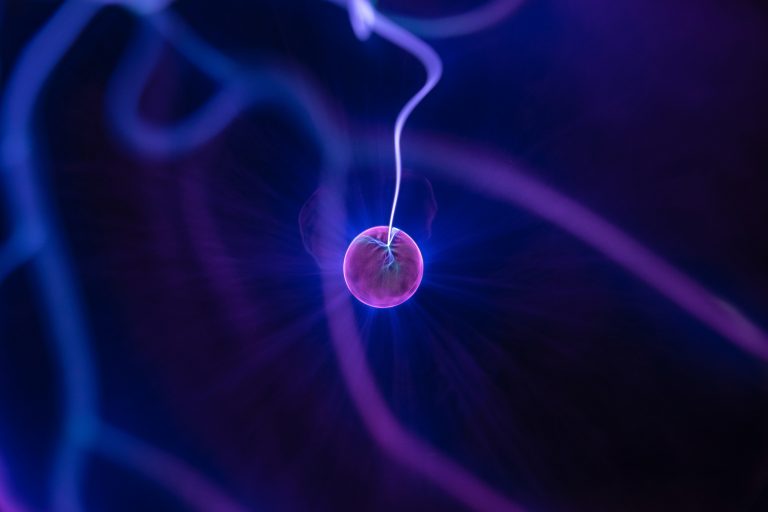政策與議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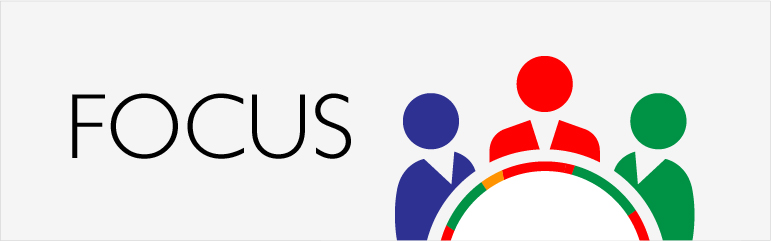
海拉細胞後面的那個女人、家庭與倫理議題
台灣受試者保護協會 理事長 林綠紅/海拉細胞後面的那個女人、家庭與倫理議題

《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》英文版封面。網路截圖
1951年2月海莉耶塔.拉克斯(Henrietta Lacks)的子宮頸癌細胞被體外培養成功,名為海拉細胞(HeLa Cells),這是醫學界的第一次。在此之後,海拉細胞廣為應用於醫學研究,應用之廣幾乎到了醫學領域學生、研究者無所不知的情況,除了她自己與她的家人。 《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》(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)一書出版於2009年,是第一本試著拼湊這位對人類醫學進步做出貢獻,但只剩代號HeLa的海莉耶塔.拉克斯曾有的活生生的人生,以及其中涉及的醫學研究倫理議題。
在海莉耶塔不知情下的醫學研究倫理
活生生的人(living individuals)在醫學研究倫理上,對照的是分離於人體的組織、檢體。海拉細胞來自海莉耶塔子宮頸組織切片,是當時癌症治療過程中,主治醫師「順便」取下,送給正進行體外人體細胞培養研究的蓋伊醫師。
以1951年的時空背景,這順便取下的檢體作為研究,到底需不需要病人同意?醫學研究中,作為研究對象的人被稱為受試者(human subject),受試者保護首次躍上國際舞台為1947年的紐倫堡法典(Nuremberg Code),其內容來自二戰後審判納粹集中營中不道德的人體試驗判決書,第一條即強調「受試者的自願同意絕對必要」,與1964年世界醫學協會(WMA)通過的赫爾辛基宣言(Declaration of Helsinki),都將受試者知情同意(informed consent)視為醫學研究倫理的核心價值之一。
所謂的「知情同意」,是指研究者應以受試者可理解的語言「適當告知每位潛在受試者研究之目的、方法、經費來源、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、研究者所屬機構、研究可預見之益處,潛在風險與可能伴隨的不適….」(赫爾辛基宣言第23條),於受試者充分理解後,自主決定是否參加醫學研究。知情同意的原則在於確保醫學研究受試者自主權,避免被迫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當白老鼠。
就如同海莉耶塔所遭遇的,參與研究對於受試者本人幾乎無益處,甚至有風險。但是,以人作為受試者又是醫學研究所必需,若無當事人同意,形同將人化約為物,損及人性尊嚴,這也是紐倫堡法典為何強調自願同意之必要的原因。不過,在海莉耶塔所處的年代,對於受試者似乎想到的都是「活生生的人」。到底對於與人分離的組織、檢體,特別是因為開刀、醫療檢查取出的人體組織,以此做研究是不是需要當事人同意?或者,這個當事人是不是也被包含在受試者保護的範疇內,並沒有規範。美國一直到1974年制訂受試者保護的法規,赫爾辛基宣言到2000年修正,才將受試者的範圍延伸至「任何可辨識之人體組織或資料」。
所以,海莉耶塔1951年生命垂危之際,被取出檢體,她自己知不知道醫師順手做了切片,切下正常細胞與癌細胞組織,而且交由與她醫療無關的醫師,進行了體外的細胞培養?顯然並不知道,當然也沒被告知。以當時的時空背景,這樣的行為在法律,甚至倫理,都屬於模糊地帶。
海拉細胞極具商業利益,海莉耶塔的家人卻負擔不起醫療費用
然而,故事並不是到此為止。海莉耶塔的癌細胞經過體外培養,成了醫學研究中的「海拉細胞」,最傳奇的是,在醫學技術正起步的年代,海拉細胞透過簡單的方式就可無限繁殖,培養、販賣海拉細胞成為一門生意。但就如同海莉耶塔女兒黛博拉所說的「……我老是覺得很奇怪,要是我媽媽的細胞對醫療這麼有用,為什麼她的家人看不起醫生?這一點道理也沒有。很多人靠我媽媽賺大錢,我們卻連他們拿了她的細胞都不曉得,到現在一毛錢也沒摸到……」(頁34)在這本書當中,另一個海莉耶塔家人屢屢質疑的問題,也是醫學研究中另一個倫理議題,關於人體細胞的商業利用後續利益的分享(配)。到底海莉耶塔的家人可不可以主張分配販賣海拉細胞所得的利益?
本書提到1980年代受到矚目的mo細胞株的案件,莫爾告他的醫師勾爾德未經同意,以他的細胞申請專利以及細胞株所有權。莫爾同時要求分享專利權所得的利益。莫爾敗訴定讞,加州最高法院認為,身體組織只要從身體移除,病患就已經不得主張權利,不論是否經過病患同意。而專利權的部分是研究者發揮才智努力發明而來,與病患無關,無權分享商業利益。不過,未告知商業利用違反知情同意原則,但當時美國法律並未明訂,法院呼籲國會應予補救。
類似的案件也在台灣發生,2010年研究者以泰雅族人血液做研究,找到原住民痛風基因,並向美國申請專利,遭人權團體與當地原住民族質疑未徵得原住民同意,侵害人權。
關於人體細胞或基因之商業利用,爭議之處其實多出於未完整告知。而其中同時涉及研究者與受試者之間的知識與專業上的不對等。「我身上的細胞,成為你賺錢的工具」,或者「我的基因,成為你的專利」,到底人類的細胞、組織或基因可否成為買賣的標的?同時,一旦基因、細胞被定價之後,原本受試者即使需以此治療疾病,可能再也負擔不起,就如海莉耶塔的家人所遭遇的。怎麼去平衡中間的落差?除了知情同意時的說明之外,由於許多醫學研究有賴於利他的受試者捐贈檢體,或公共資源的挹注研究,方能獲得成果,部分商業利益回饋社會亦是平衡落差的方式之一,2003年國際人類基因數據宣言(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n Human Genetic Data)關於基因研究獲得商業利益,提出的利益共享方式包含:對參與研究的個人和群體提供特殊幫助、提供醫療服務、 提供科研得出的新的診斷方法、新的治療設備或藥品、支持衛生事業等等,這些作法的目的,不外乎是為減少社會弱勢群體無法享受醫療研究帶來的新醫療技術,但卻在研究階段負擔了成為受試者的風險,以及減緩新穎的治療方式所需高昂的費用,而產生的健康不平等。
那些被實驗的黑人、兒童及心智障礙者
海莉耶塔的遭遇是否只是個案?1966年Henry Beecher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發表「倫理與臨床研究」(Ethics and Clinical Research )一文,批露了22 例於知名醫學期刊發表的醫學研究,未告知受試者,或者未告知風險,不符倫理的情節嚴重,引起社會一陣譁然。這其中許多個研究的受試者是兒童、心智障礙者或老人等弱勢者。海莉耶塔的大女兒艾兒西疑似心智障礙,因為照顧不易,被送至克朗斯維爾醫院,15歲死於該醫院。而當時這家醫院同時也是大型的心智障礙者收容機構,被揭露以病人進行氣體腦部研究,而幾乎所有病童都在無父母親或家屬的同意下被當實驗的對象。另一個為人熟知的醫學研究醜聞「塔斯基吉梅毒實驗」(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),則是美國公共衛生署自1932年起,於阿拉巴馬州招募黑人進行梅毒不加治療的實驗,但受試者多為不識字的黑人,也未被充分告知研究的意旨,因而不理解固定的回診、抽血並不是為治療他們的疾病,而是為觀察梅毒的病程,也導致傳染給配偶或垂直傳染下一代。這個不道德的研究,直至1972年被媒體揭露才停止。1997年美國總統柯林頓為此案造成的傷害向倖存者道歉,表示:「聯邦政府做了嚴重、深切且是道德上的錯事。」
無論海莉耶塔、艾兒西,或其他在這些醫學研究中受到侵害的人,多數都是弱勢者。在受試者權益未被認真對待的年代,輕易地被當成人類白老鼠。這些不忍直視的醫學研究醜聞的犧牲者,同時推動著人權議題往前走,1970年代起國際間受試者保護的倫理、法規往前邁出第一步。
太多還是太少?女人作為受試者
然而,在性別議題上,醫學研究卻顯然往了相反的方向。1970年代Dalkon Shield 子宮內避孕器感染導致無法生育、子宮外孕,甚至死亡。因此,1977年美國FDA(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)修正臨床試驗的指引,限制招募育齡女性參與早期藥物臨床試驗,除非是威脅生命存續的重大疾病藥物臨床試驗。這也導致醫學研究中招募女性為受試者的比例開始降低。除了法規上的限制外,女性賀爾蒙的週期,常被認為會干擾研究成果的判讀,因而傾向不招募女性為受試者。然而,對女人來說,如在藥物研發階段女性受試者比例不足,如何判斷女性用藥的劑量與療效。同時,有越來越多研究顯示,疾病、藥物使用都有性別差異,如研究階段將女性排除,則藥物上市後安全性、療效堪慮。雖不斷有婦女團體倡議,但女性受試者比例仍舊偏低。這也是近幾年來,台灣婦女團體關注的性別與健康的議題之一。
歷史很遠嗎?其實沒有
海拉細胞背後糾葛出醫學研究中的倫理爭議、階級與種族等議題,表面上是發生在上世紀的事,但其實這些議題仍有不同變貌的進行式,最近發生在中國的基因編輯愛滋嬰兒事件,其中受試者是否完全知情且同意也引起爭議。以人為受試者仍是目前醫學研究的必要,但如何使海拉一書中的爭議場景不再發生,這是關上書後,我們必須深思的。
推薦閱讀:
- 芮貝卡.史克魯特《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》(內容連載),衛城出版。
- James H. Jones《髒血:塔斯基吉梅毒實驗》,群學出版。
- 霍恩布魯姆《違童之願:冷戰時期美國兒童醫學實驗秘史》,生活‧讀書‧新知三聯書店出版(簡體中文)
- 台灣女人健康網